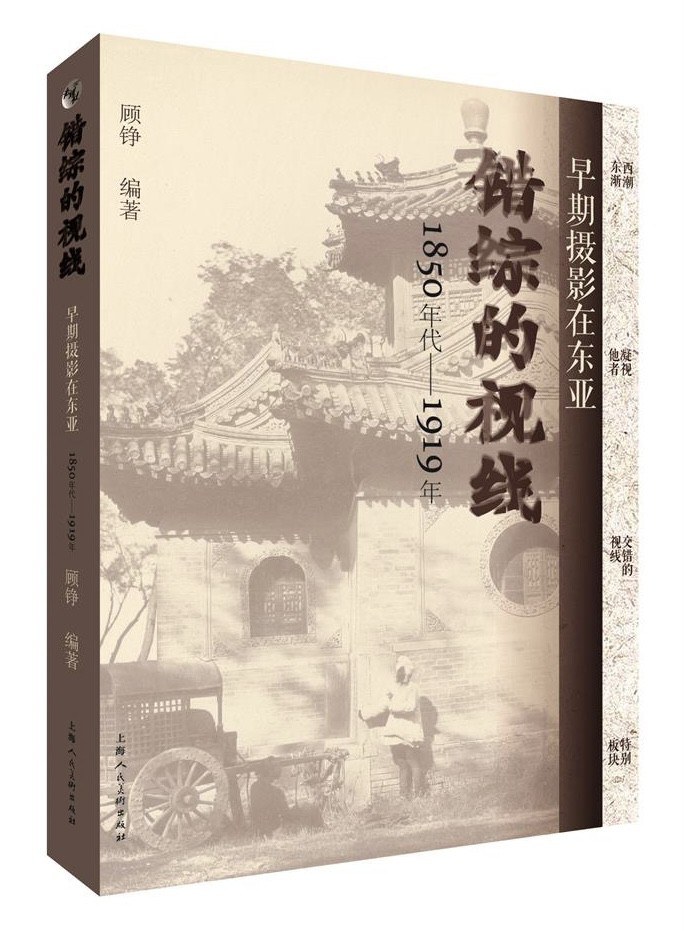
《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顾铮编著,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4年6月版,298.00元
在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中,如何突破固化的国别视角、激活跨国扩展的研究视野,这是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方向。在这里遇到的难题除了需要在跨国、跨文化语境中更多挖掘、整理历史照片之外,还需要在摄影者身份、摄影行为的历史记载以及照片的传播方式等史料研究方面下功夫。在跨文化研究语境中,一次成功策划的研究型摄影展览将是有可能产生突破性成果的重要机缘,在征集、整理、展示和研讨过程中的学术交流必然可以促进产生更多不同视角的个案研究。
顾铮编著的《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24年7月)是2023年谢子龙影像艺术馆馆藏研究展《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的同名文集。该展览以费利斯·比托(Felice Beato)以及其他一些西方摄影师的东亚摄影作品为中心,结合包括来自国内外其他机构和个人收藏的摄影和视觉作品,尝试综合展示早期摄影在东亚的发展状况,努力争取在跨国别、跨文化的多角度、多层次、多媒介——这正是所谓的“错综的视线”——中描绘早期东亚摄影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毫无疑问,由西方引入东亚的摄影术,既是一种技术观看与存像的新方式,同时也是一种以照片为主要形式的新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手段。在这些摄影作品中既展现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以及抱持不同目的的摄影者眼中的东亚历史文化和社会现实,也展现东亚早期摄影的自身状态,是从“内史”与“外史”相结合的层面上探索全球帝国主义时代里发生在东亚,尤其是中国的摄影实践的作用、意义和价值的重要研究议题。
该文集分为两大部分。论文部分除了顾铮撰写的《策展人语》《东亚及其摄影表征——从策展“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说起》和《丁悚与上海五四运动》之外,还收入了其他学者的论坛发言选粹或论文:《真实、拷问与错值:中国当代摄影与“红色图像”》(王璜生)、《相机、照片、写生与心印——青年画家孙宗慰眼里的西北边地民族,1940年代》(曹庆晖)、《东亚作为方法与奇观》(吴盛青)、《Z世代历史影像的跨文化传播——以推特、Instagram为例》(仝冰雪)、《创建西德尼·戴维·甘博的数字藏品库》(周珞)、《漂浮的政治:普拉特东亚相册中的空间与体验 (1874-1900)》(袁昕玥)。图版部分分为“西潮东渐:大变局中的东亚景象和图像”“凝视他者:来自西方的摄影观看”“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等四个板块的章节内容,向读者呈现出五百六十余件包括照片、浮世绘、明信片、年画、版画、油画、画报等多种视觉样式的影像艺术资料。因此可以说是一部图文丰富的学术研究文集。
顾铮在“策展人语”中首先解释了出现在展览标题中的“东亚”是一个历史地理概念的东亚,包括中国、日本和朝鲜半岛。应该说,作为历史地理概念的东亚与在1920年代在日本出现的具有强烈文化与政治意味的地缘政治学的那个“东亚”概念的确是必须区分开来的。子安宣邦曾经指出,“为了能够重谈这个‘东亚’概念,我们必须弄清楚与帝国日本一起诞生的这个概念的谱系,必须看清这个概念的消亡过程。不如此,我们就无法保证重新兴盛的这个概念,不会成为由帝国日本主导的亚洲广大区域之幻想的死灰复燃、不会再出现帝国亡灵式的话语”(子安宣邦《东亚论——日本现代思想批判》,赵京华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93页)。也正是在历史地理的概念上,历史学家堀一敏曾经强调希望“把包括中国、朝鲜和日本在内的东亚地区,视作具有一定的结构的历史世界来把握”(见堀敏一《隋唐帝国与东亚》“前言”,韩昇、刘建英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这都是把“东亚”作为突破国别史局限的历史地理概念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另外我也注意到顾铮在《东亚及其摄影表征——从策展“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说起》一文中谈到了日本近代美术史权威学者和著名思想家冈仓天心(1863-1913年)的《东洋的理想:建构日本美术史》(英文1903年初版,1917年法文版、1922年德文版,各种日文版也先后问世),认为冈仓天心的“亚洲一体论”既有理想主义色彩也有帝国主义的理想。这也是关于“亚洲论述”中值得思考的问题。应该说,冈仓天心对“亚洲强国”概念的念念不忘和对日本使命感的反复强调,的确会使人怀疑其思想与后来的“大东亚”军国主义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但是从冈仓的著述本身来看,“今天日本作为亚洲强国,必须自觉地认识到历史赋予我们的重大责任。我们的使命不仅是要复兴自身的古代之理想,同时还要去唤醒整个亚洲,唤醒至今沉睡的所有一切。我们要把印度的宗教和中国伦理道德提高到更高的阶段,以克服西方文明所带来的各种弊病”(116页)。在最后一章“展望未来”中,冈仓指出“亚洲的思想、科学、诗歌、艺术中蕴藏着一种力量。如果亚洲人抛弃了自己的传统,印度将失去国民宗教生活的精髓,堕落为卑贱、虚伪、迷醉于光怪陆离的国家。中国若只去追求物质文明而取代精神文明,它将会失去古老国家的传统尊严与道德伦理”(124页)。因此这种“唤醒”的关于文明的使命感看起来与军国主义政治还是有很大距离的。
顾铮认为,“由西方引入东亚的摄影术,作为一种技术观看与成像和存像的新方式,同时作为一种以照片为主要形式的新的知识生产和文化传播的手段,在深入观视东亚、建立帝国主义的东亚想象的过程中发挥了其应有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进入到了东亚的摄影观视技术,如何被本地区的人们自主地运用,记录保存其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以及区域内人们如何相互观看的实践。确确实实,展现在本展览中的复杂交错的观看视线,其质地、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也体现观看者各自的现实与历史意识和视觉念想”(第2页)。在该书收入的连“序章”共四大部分展览照片的安排和题目中清晰地反映了策展人的这种展现“复杂交错的观看视线”的意图:序章是“西潮东渐:大变局中的东亚景象和图像”,第一部分“凝视他者:来自西方的摄影观看”,第二部分“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以及包括了“出洋留影”“口岸风景”以及“相关文献”在内的特别板块。展出作品以约翰·汤姆逊在1850年代的亚洲及中国摄影为起点,以丁悚与西德尼·甘博等人所见1919年五四运动为终点。除了照片为主要形式外,还包括了浮世绘、明信片、年画、版画、油画、画报等多种视觉样式。很显然这是一种跨视觉媒介的呈现方式,以此展示来自东西方的多重摄影观看以及交叠视线之下的东亚摄影观看实践中的东亚社会人文景观。
关于这种展览结构的安排,我想起了葛兆光教授在《亚洲史的研究方法:以近世东部亚洲海域为中心》(商务印书馆,2022年)中谈到“亚洲史的研究方法”问题。他强调了三个方面:一是超越国境,从对“亚洲/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整体认识重新研究中国;二是要把“艺术”“宗教”“历史”三个领域综合起来,充分使用文献、图像和考古发现的资料进行研究,把对历史与文化的认识贯通起来;三是要在全球史研究的背景下以“全球史”的角度、视野和方法来研究“东部亚洲海域”的历史。这样的研究视野和方法从史学研究观念上说就是要重视“文化接触”的研究趋势——“也就是不同文化间的相互影响、接受与转移,边缘对中心的影响,以及从边缘重思世界史,强调联系、互动、影响的全球史”(第6页)。在论述“东部亚洲”为何成为一个历史世界的时候,他也强调了要把图像看作是一种构成共同文化的要素,从图像的主题、风格、技法、审美习惯等多方面论述了艺术是把东亚联系为一个历史世界的“要素”。
在我看来,这个题为《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的展览正是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从东亚历史的整体性认识切入中国早期摄影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如果展览能够激活我们对于思考和反思摄影自身在一个跨国扩展的过程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摄影跨国观看实践所内包的视觉政治和不平衡的力学关系,以及同时产生的可能至今不衰的,影响我们的世界认知的某种历史影响和作用,那么这个展览的实现,相信对于国内外视觉文化以及摄影研究的发展会有一定的促进意义。”(第3页)应该说,这是可以肯定的成果。
但是关于“错综的视线”本身,既是一种有效的研究视角,同时也并非可以完全不受干扰的。研究者语境的问题在这里仍然会起着某种制约作用。作者对于“摄影观看‘简化’世界的局限性”以及不得不经过选择才能展出这样的展览机制始终怀有清醒的反思与警惕之心,“在选择这些照片的时候,我意识到了些什么?我意识到哪些东西不能够在这个展厅中展出,我有什么样的战战兢兢?因此最后出现在我们眼前的这么一个展览,虽然是规模空前的500多件作品,但是是经过不断地简约,不断地基于客观的个人主观性的介入所形成的展览”(11页)。这里涉及研究者与展览策展人所处的具体语境问题,由此决定了在“错综的视线”背后存在的令人感到遗憾的“视差”——总有一些东西仍处在视觉盲区之中。
关于“观看的多重性以及主体性的‘唤醒’”是一个重要议题,顾铮认为摄影观看既是一种新的知识生产的方式,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认知可能性。“对于展览里的由‘帝国之眼’所处理的作为‘他者’的东亚照片,我们可以发现来自西方的观看具有某种掌控性,因此也具有某种压迫性,有一种视线威慑的性质在。……但是,观看从来不是单向的。‘看’既是一种具压迫性和胁迫性的行为,同时‘看’也是一种唤醒。”(第8-9页)因此展览的第二部分“交错的视线:东亚内部的自审与互视”展示的就是掌握了“看”的技能和方法的中国摄影师开始记录自己现代化进程中的努力与实践,包括了京张铁路摄影、丁悚拍摄的中国现代女子教育与美术教育的照片,以及作者不明的上海五四运动照片。在这里,作者希望引起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在东亚摄影中“错综的视线”的主体性问题。
顾铮在论文中还提到了2022年12月到2023年8月新加坡国立美术馆主办的《活着的照片——摄影在东南亚》,认为相互之间有一种呼应关系,即以摄影为途径做地区思考与展览,用一种区域“联动”(linkage)的方法来尝试展示不局限于一国之内的一些摄影实践。目的是探索“以一种有所超越现代民族国家国境的方式来思考摄影的历史及其实践”(12-13页)。刚好我去年我在参观新加坡国立美术馆的时候买到了这个展览的图册“Living Pictures: Photography in Southeast Asia”(National Gallery Singapore,2022),发现这两个展览之间的确有一种共通的不谋而合的学术意图。《活着的照片——摄影在东南亚》策展人Charmaine Toh在论文中说,该展览充分考虑了摄影在影响我们看待和接近世界的方式方面的力量,以及自十九世纪中叶摄影进入该地区以来,摄影在知识和表现系统中的动员力量。这次展览为研究全球摄影史提供了另一条线索(p.8)。他在论文的结论部分强调指出,这个展览的最后部分尤为明显地呈现了通过艺术塑造的摄影话语位于一个特殊的节点上,“它借鉴了乡土摄影、工作室肖像、调查文件、新闻摄影等,从而为我们提供了最大的讨论和干预空间。归根结底,这是一场关于摄影想象力的广阔范围以及这种想象力的影响的展览。……从19世纪至今人们对东南亚的看法,到现代身份的主张和对国家历史的重新审视,摄影艺术已经并将继续推动人们看待和理解东南亚的方式”(p.13)。如果联系到前面顾铮提到的关于展览机制的局限性问题,那么《活着的照片——摄影在东南亚》所呈现的摄影在历史实践与在东南亚地区产生的视觉政治意义方面无疑还是超过了“错综的视线”。
杜克大学周珞教授的论文《创建西德尼·戴维·甘博的数字藏品库》介绍了美国社会学者与中国研究学者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 1890-1968)的照片数据库中每张照片的标题和地理名称信息的标准化整理工作,谈到了甘博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敏锐观察者”:“他记录了制度方面的变革(如新式的学校、监狱和医院等),新交通工具的出现,最珍贵的是他捕捉到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不同阶段的生活状况。数据库中的大量反映中国生活场景和各行业人物的照片也出于他在北京进行的社会调查工作。甘博对北京社会的调查是中国最早的社会调查,反映了他对中国人民和他们的文化的好奇和共情。”(40页)而在建立数据库的过程中,如何创建照片的图像标题和地理标签面临不少困难。作者通过一些照片详细论述了创建标题、地理标目以及中文翻译的过程和方法,本身就是历史地理学和历史图像学研究的重要例证。比如“So Village”名称出现在编号是44A到51A卷以及17B到19B卷的胶片上,拍摄地点肯定是在四川茂县、汶川县和理县这一地区。最初的猜测“So Village”可能是“索村”或“苏村”,但在该地区找不到这两个名称。有两张标示为“So Village”的两张照片分别展示了一个独特的塔楼结构和一个位于门楼顶部的保护神雕塑。作者根据一位博客的文章提供的重要线索并进一步查阅了当地历史文献,最后确认了这个村寨位于汶川县,当地居民主要是很久以前从西藏迁移到这里的嘉绒藏族。嘉绒人相信他们是大鹏鸟的后代,因此以大鹏鸟作为他们的图腾。第二十任瓦寺土司在乾隆皇帝的封赐下获得了“索诺木”这个姓氏,后来被简化为“索”。甘博在这个村寨里拍摄了索土司及其儿子的照片,照片中父子俩都穿着典型的汉族服装(36-37页)。
加州大学博士候选人袁昕玥的论文《漂浮的政治:普拉特东亚相册中的空间与体验(1874-1900)》的研究对象是洛杉矶盖蒂研究中心收藏的一本十九世纪摄影相册,主题多是中国和日本的风光照片。相册的主人是来自法国的吉·普拉特(G·Prat),一位受雇于美国和英国洋行负责生丝贸易的普通职员,他于1877到1884年期间在广州生活。该相册中的大部分照片都并非他亲自拍摄,而是向中日商业摄影师购买而来,他本人也将当地摄影师的照片出售给其他短暂经停广州的欧美旅行者。特别有意思的是,视觉政治的研究意义也产生在这批照片之中。“除了自然灾害之外,政治暴力事件也威胁着沙面岛的安全。19世纪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是一场空间的角力。沙面岛洋行建筑本身往往被当地社群视作是最理所当然的攻击目标。1883年9月10日,在中法战争(1883-1885)的背景下,当地民众袭击了沙面岛东侧的建筑,许多建筑被破坏和焚毁。相册第55到68页集中收录了1883年暴乱之后的一系列废墟照片。如果不是相册页的文字说明,我们很难辨认这些残骸曾经是普拉特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的场所。……不过,在第64页和第65页的注释中,普拉特以镇定和客观的语气叙述了这场骚乱,仿佛书写能够帮助他平复和掌握失控的局面。”“在1883年9月这场沙面暴乱发生的一个月后,美国著名艺术收藏家和环球旅行家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嘉纳(Isabella Stewart Gardner,1840-1924)来到广州。她的旅行日记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本文所讨论的诸多问题。”(59-60页)这些图像显然也是研究中法战争背景下的广州民族主义运动的重要史料。
顾铮在《丁悚与上海五四运动》中首先考证了丁悚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的上海五四运动照片可能是由照相馆派出摄影师拍摄的,并由在《神州日报》社任美编的丁悚保存了下来。在去年顾铮策划的“慕琴生涯——丁悚诞辰130周年纪念文献展”中,在展示了丁悚收藏的上海五四运动照片的同时,还展示了西德尼·甘博拍摄的北京五四运动照片、丁悚在当时发表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时事漫画以及当时上海画家赵藕生描绘上海五四学生运动中两个女学生在街头分发传单或报纸情景的月份牌作品。通过这样的同时展示、对比分析和挖掘其历史内涵及意义的方式,不仅是对丁悚的历史贡献的重新认识,而且在对于甘博拍摄的北京五四照片与上海照相馆拍摄的五四运动照片的风格比较中发现了两者之间在摄影手法与语言的运用方面的明显区别。不过在上海的这批照片中,我认为也有一张有比较重要的新闻报道意义,就是那幅《五四运动中上海拆除“仁丹”招牌的场景》(244页),一个男子爬在梯子上正在拆“仁丹”招牌,下面路人驻足仰头观看。另外也发现当时颇负盛名的画家赵藕生(1888-1944)在绘制五四学生运动的形象和情景时颇多参考照片,结论是“从这张画,我们也可以发现更多当时新闻报导摄影与绘画的互动”(69页)。在这些互动中产生的视觉政治更具有丰富、复杂的历史内涵。
乔治·弗朗西斯(George Francis)早在1888年就呼吁系统地收集摄影照片,认为它们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充分地描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他说的就是从历史史料的角度看待摄影照片。中国摄影史研究与撰写的新发展阶段,是摄影史越来越走出传统的研究视野和叙事框架,多元视角和跨区域的研究逐步引起重视,其中摄影与近代历史、区域发展乃至殖民地研究等“错综的视线”正在引起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这次《错综的视线:早期摄影在东亚(1850年代-1919年)》展览就是很好的研究成果。
还应该指出的是,在我尤其关注的历史图像学研究中,这些早期东亚摄影照片可以具有双向的激活意义:既能激活近现代区域历史研究中的想象力,同时也可以激活关于中国早期摄影史叙事体例和图像解读策略的想象力。前者帮助我们想象和建构一个形象的区域历史图谱,后者使我们的早期摄影史研究进一步打开“外史”的开放视角,在图像解读中保持开放的精神。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