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部的尊严感就在于思想。
——帕斯卡
排斥平庸市侩的人
朱利安·拉斐特出生于尼斯,是一位年轻的科学家,正在研究克莱蒙费朗周围的火山。他的父母都是心理学家,且终身为法国共产党激进分子。他离开尼斯去波尔多攻读研究生,之后在克莱蒙费朗工作了六年。他看上去有点像朋克,但很有风度。
与本书开篇提到的迪迪埃、约翰和卢一样,朱利安非常重视生活的审美层面。他对那些文化见识短浅的科学家同事表现出极大的蔑视。他容易感到无聊,对品位差的人毫无耐心。朱利安择友十分谨慎,因为他需要跟朋友有心智上的共鸣,并能畅谈政治话题。他无法想象和右翼分子成为朋友。这也是他与顶头上司处不好关系的部分原因,他将其描述为跟自己完全不同的人:这位科研主管热衷于金钱,喜欢看轻歌剧和商业大片,而且“对艺术文化一窍不通”。
朱利安感觉自己比某些人优越,诸如那些“一天不落地看电视”的人,随波逐流、“从来没有政治立场的人,三句话不离钱的人,还有那些每到八月就去海边度假的人,两年换一次车的人……他们不会独立思考,对电影、唱片、戏剧、展览永远没有自己的见解。他们从不表达观点,甚至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
朱利安是文化排他者的一个理想型范例。像他这样的人,通常基于才智水平、受教育程度、世界主义和精雅程度来评估人的地位。他们在这些方面感觉到优越,看不起那些“眼界狭隘、连报纸都懒得看的人……除了孩子的事和自己的高尔夫球赛,一无所知”(印第安纳波利斯某律师),那些“在才智上跟我不对等”或者“未充分发挥自身才智”的人(印第安纳波利斯某数据经理),还有那些“不动脑子,从不自我提问……满足于眼前的一切,对什么都盲目接受的低能儿”(克莱蒙费朗某哲学教授)。与朱利安一样,在讨论他们欣赏的朋友的品质时,这些人较少提及为人诚实或世俗上的成功,而是更多地谈到有趣的灵魂、世界主义的眼界和精雅的品位。他们欣赏能够激发自己的求知欲和创造力的事物,甚至可以将成功定义为 “保持智性的活力”(印第安纳波利斯某计算机专家)。
访谈表明,文化因素是两国高等地位信号定义的核心。然而,从受访者在文化维度上的定量排名可以看出,与法国人相比,文化边界对美国男性受访者来说重要性稍低。当被要求在23个性格特质中选出自己最看重的品质时,他们的选择反映了这种差异。有24%的法国人和6%的美国人认为才智优越是列表中最重要的性格特质;类似的结果还有,22%的法国人和仅6%的美国人将思想狭隘视为最负面的个人性格特质之一。最后,有52%的美国人将世界主义描述为一种让他们无动于衷的性格特质,而这类法国人只占30%。这一调查结果有重要意义,因为在研究美国文化资本的文献中,高等文化地位信号被视为美国中上阶层文化的核心。我的数据表明,对此种观点尚须进行细致的分析,毕竟有相当多的美国专业人士和经理人都以较为批判的眼光来看待智性主义、世界主义及其他高等文化地位信号。
本章的前半部分探讨法国和美国中上阶层成员如何定义才智水平、自我实现和文化修养,以及他们在谈论地位评估时如何运用这些维度。与前几章一样,我们将指出两国中上阶层成员使用高等文化地位信号的重要差异,例如,这两个群体以不同的标准评估才智和文化修养程度,同时,美国人比法国人更强调自我实现。我们还将看到,大多数人所运用的高等文化地位信号比文献中最初提出的范围要广得多。事实上,虽然有关文化资本的研究大多强调语言能力、掌握高雅文化和展示有教养品格的重要性,但访谈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才智和自我实现也在文化地位评估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在本章的后半部分,通过比较法国和美国各自的优势和知识分子亚文化的差异来分析两国文化边界的特点。数据表明,法国的知识分子亚文化比美国的更有凝聚力,这进一步证明了文化边界在法国的重要性。此外,两国的文化边界具有不同的形式结构:法国人运用的边界更稳定、更普遍、更等级化,而美国人运用的边界较弱。美国人比法国人拥有更广泛的文化剧目,他们在文化上更宽容,更多地表现出文化自由放任(cultural laissez-faire),因为他们对“好”品位和“差”品位的区分不那么具体,而是比较模糊和不稳定的。这印证了文化边界在美国语境中的重要性较低。它还表明,两国的文化边界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有所不同。因而,如最后一章将指出的,相比法国人,美国人在话语层面上划定的文化边界较少可能转化为客观的社会经济边界。但是,首先我要探讨这两国人划定文化边界的信号类型。

巴黎花神咖啡馆
文化排他、才华、专业知识及其他形式的才智表现
鉴于大学教育和专业知识在确定中上阶层成员身份中的重要性,因而并不奇怪,受教育水平和才智的差异是两国受访者在划定文化边界时最常见的两个基点。事实上,有很多人,甚至包括那些并不自认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当谈到希望结交什么类型的人时,都很看重才智。他们一再将自己的朋友和最喜欢的同事描述为既聪明又能激发思考的人。他们这样描述自己感兴趣的人:“具有一定知识水平”的人(纽约某律师);“善于思考,或者说试图去认真、严谨、有逻辑地持续思考的人。他们优于那些思维不连贯或拒绝思考的人”(巴黎某文学教授)。这些群体也很重视高等教育,正如有关教育和地位获得研究的大量文献所指出的,高等教育是获得中上阶层地位最重要的门槛,无论是从工作机会还是从融入社交圈的角度来说都是如此。
我访谈的法国人似乎特别关心才智,他们反复申明自己很难容忍愚蠢。同样,他们谴责愚蠢(la bêtise)的强烈程度,只有美国人对无能的抨击可与之匹敌。如凡尔赛的商业管理专家路易·杜邦所说,愚蠢是最严重的罪行,远比不诚实更甚:
思考问题并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是生活中最⼤的乐趣之⼀⋯⋯现实中存在的平庸和愚蠢程度令人惊愕。我更愿意和狡猾的聪明人打交道,因为⾄少我们能够相互理解。倘若他们不诚实,那不是我的问题。一个蠢货才真让我无可奈何。
本章前面提到的物理学家朱利安·拉斐特也认同这一观点。对于朱利安来说,不诚实的人不像思想狭隘的人那么糟糕,因为“和不诚实的人仍有可能进行交流。有可能把他带回正确的方向。而面对思想狭隘的人,你真是束手无策”。这种明确将文化标准置于道德标准之上的观点,美国的受访者中没有一个人表达过。
法国受访者对才智的格外关注也反映在对英雄和榜样的描述中:伟大的知识分子,如雷蒙·阿隆(Raymond Aron)、雅克· 阿塔利(Jacques Attali)、让- 保罗· 萨特(Jean-Paul Satre)均占据了一席之地。受访者中的一位,克莱蒙费朗的博物馆馆长雅克·孟德尔,表达了一种普遍的感受,他承认经常这样作自我评估:“那些智识水平在严格意义上超越我的人,令我感到自己很渺小……因为我觉得他们在我试图取得成功的领域获得了成功。”归根结底,对于这些人来说,智力成果才是最卓越的成就,远远超出了金钱和它所能带来的世俗的成功。法国社会的一些特征反映了这种信念。仅举一个例子,法国的许多政要都撰写过严肃的政治论文;他们非常有兴趣在智识方面受到尊重,并从参与巴黎的知识分子生活中获得声望。
我的法国和美国受访者通过截然不同的文化范畴来理解人的才智(正如同他们理解诚实的方式)。法国人强调要有一种批判意识,这被视为衡量一个人分析能力的标准。他们还通过智力玩笑、抽象能力、口才和语言规范来解读才智。相比之下,我们看到美国人主要关注的是实际能力。正因如此,他们主要将专业知识视为才智的体现,非常重视“了解事实”,最重要的是了解“相关的”,即有用的事实。我将在下文中依次讨论这些跨国差异。
在法国的笛卡儿主义传统中,知识来源于系统地怀疑假设和公认真理的能力。无论个人付出多少代价与努力,最重要的是,获取知识需要具有质疑权威及寻求真理的能力。因此,拥有才智的标志是有批判意识和一定的智性诚实,即“不循规蹈矩,有能力理解各种情况并表达个人观点,同时与一切社会从众行为保持距离”(巴黎某社会工作者)。粗鲁型的人是不可能具有批判意识的,他们不“仔细分辨自己的思想,不思考;只是在道德上保护自己。他们自以为无事不知,无事不晓”(巴黎某律师)。在大西洋此岸,笛卡儿怀疑论可能被视为具有过度批判倾向或是缺乏灵活性的象征,美国的受访者很少谈及批判意识,除了一向与欧洲智识遗产联系紧密的少数犹太人。这种批判意识的重要性及其所暗示的对心灵生活的魅力( 和普罗米修斯精神), 部分是由精英高中的毕业考试(baccalauréat)所要求的哲学教育功底支撑的。私立天主教高中(相当大比例的中上阶层子女去那里就读)都非常强调哲学思维训练。这种环境间接地鼓励学生们将修辞学当作一种智力游戏,在其中展现自己的机智、灵活和敏捷;推理能力,包括抽象能力、表达能力以及阅读的广度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掌握事实则不受重视,因为学生们学习的是如何在理论基础上建立复杂的论点。建筑学教授迪迪埃·奥库尔的态度体现了人们对求实精神(factualism)的普遍反应。当被问及消息灵通对他来说是否重要时,他答道:“我完全不关心这个。时事是无关紧要、转瞬即逝的知识流动。”
有这样一句名言:“法语是最精确的语言”(What is not clear is not French)。法国的知识分子传统非常强调思维和表达的清晰性,这被视为才智的进一步标志。一位受访者(巴黎某人力资源顾问)在描述“句子之间的平衡,注意选择词汇及其确切定义,以及它们蕴含的基本思想”的重要性时,简直到达了抒情的巅峰。在另一个场合,一位受访者对我说:“糟糕的语法暴露出思想的粗鄙。”有不少人指出我的调查问卷中有一个拼写错误,显示他们是法语的忠实信徒。在谈及才智为何物时,两国受访者的语气也戏剧性地突出了相互竞争的概念:美国人的回答往往简短而中肯,而法国人尤其是巴黎人的回答,明显地更长、更复杂、更富有细节和自我反思的评论。
法国教师运用的评价标准反映了这些不同才智信号的重要性。事实上,演讲风格、口音和措辞等方面,对各级学生的表现评估均有很大影响。对语言的娴熟掌握是被社会推定为才华出众者的关键,尤其是考虑到法国的教育体系没有采用国家标准化的能力倾向测试(aptitude tests)。
这种对口才的强调也扩展到了专业互动领域,法国人在职场中经常唇枪舌剑,就像美国人每天都通过展现业绩来竞争一样。因而,口才这门以智取胜的技艺被锤炼得炉火纯青。此类竞争形式也有其弊端。巴黎的一位老外交官向我描述了其行政部门里的精英同僚,他们毕业于著名的法国国立行政学院(Ecole Nationale d'Administration)。他不大看得上这些人,因为:
他们并不是什么都懂,但就是有本事在不懂的情况下侃侃而谈。这真让我感觉不舒服。你让他们应对⼀件事,对此他们一无所知,但也能不懂装懂地发表⼀番意见。
在这种环境下,要想成为被社会推定的才华出众者,其关键并不一定是拥有专业知识。我们发现,即使在工程学院里,专业能力也并未获得高度重视。那些最负盛名的学校引以为傲的是向学生提供一种通用的分析方法,一套理论工具,使他们能够游刃有余地应对一系列的问题。近年来,高等教育机构发生了许多变化,引入了强调专业化的课程。然而,笛卡儿式的智识传统似乎依旧影响着法国人理解和感知才智的文化范畴。例如,在法国的工作场所,文化资源,譬如抽象而不失优雅地表达自我的能力,对成功至关重要。文化边界本身在社会不平等的再生产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高等地位信号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美国职场中诚实、友善和冲突规避所占据的地位,使得文化在整体上比道德更能决定成就的高低。由于法国职场高度重视的道德人文主义与人文主义文化本身(或曰文化地位信号)是不可分割的,这一点得到了加强。
法国人用于定义才智的范畴与美国人的范畴形成了鲜明对照,后者主要是围绕实践知识和对事实的掌握来组织的。我们看到,美国人钦佩能力。因而他们将才智解读为以合乎逻辑、清晰可行(不必讲究优雅)的方式呈现、组织和分析具体事实的能力。这种求实精神在美国人谈及自卑感的时候出现过,以长岛的汽车租赁商克雷格·尼尔的表述为例:
那些触及我的知识盲区的⼈让我感觉不舒服。比方说,如果我坐下来跟股票经纪⼈⻓时间交谈,我多半会感 到不自在,因为我对股票业务一无所知。如果有人和我坐下来讨论建筑设计,我也会坐⽴不安,因为我对建筑设计⼀窍不通。
专业知识既能打开边界,又能关闭边界。事实上,它一方面可以用来显示优越感,从而让其他人“感到不自在”;另一方面,我的美国受访者常常将他们觉得有趣的人定义为掌握 “丰富的信息”;这些人“不一定发人深省,但一定会令人振奋;他们了解自己做的事,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人,懂得如何融入社会”(纽约某环境专家)。在这里,用以区分“自己人”和“其他人”的界限不再是批判意识和得体的谈吐,而是掌握 关于世界的广泛信息。正如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招聘专家向我们解释的:
我受不了那些不谙世事,对历史、地理或时事⼀窍不通的人。我甚⾄都不要求他们对体育运动有很多了解。但⼀个⼈假如在其他方面知之甚少,懂点体育也会很有帮助⋯⋯我有⼀个好朋友,是我的邻居,他对体育不感冒,去年在看I.U.(印第安纳⼤学)全国冠军赛时居然睡着了。但我仍然喜欢他,因为他关注时事,⽽且熟知历史。这就在三个,或者说四个领域里占了两个。
美国受访者的阅读类型也揭示了美国中上阶层文化对专业知识的欣赏。与法国人相比,他们对杂志和行业出版物更感兴趣,这能帮助他们随时了解自己专业领域的最新发展,并据此作出明智的购买决定。纽约的一位娱乐业专业人士的阅读品位很有代表性:“(我)喜欢阅读……体育杂志、服装目录和房产目录;你知道,就是关于住宅、房地产、抵押贷款之类的小册子。有时为了消遣,我也会读纪实文学或自传。”常被提及的出版物还包括《消费者报告》(Consumer Reports)、《汽车与司机》(Car and Driver)、《体育画报》(Sports Illustrated)和各种计算机杂志、专业杂志和时事杂志。约翰·克雷格——上一章中提到的纽约那个疲惫不堪的市场营销专家,当谈到他妻子的读书时机和动力时,也为我们勾画出了很多人的阅读习惯:“只有当受到什么事情的激发,或是需要查找资料时,她才会读书。比如最近我岳母重病卧床,正在接受临终关怀,她就开始阅读相关的书,了解临终关怀到底是怎么回事。”访谈结束后进行的一项关于如何打发闲暇时间的问卷调查显示,法国的受访者比美国的更倾向于将自己定义为经常读书的人(有72%克莱蒙费朗人认为自己经常阅读,巴黎人有77%,而在纽约人中这一比例为44%,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人中为58%)。
这种对信息的欣赏有时会与对知识的量化追求挂钩,即强调阅读书籍和已知事实的数量。举例说,畅销杂志《读者文摘》(Reader's Digest),《危险边缘》(Jeopardy)之类的益智问答电视节目,《智力棋盘》(Trivial Pursuit)等派对游戏,都表明追求量化知识和求实精神是很受欢迎的。当然,也有相当多的美国人并不参与这些,但它仍是美国文化景观的一个鲜明特征,这是法国所不具有的;法国人的那种注重抽象和措辞的方式对美国人来说意义甚微。
我在上文中提到过,美国受访者对才智的看法也比法国人更实际。举例而言,当你问及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和榜样时,他们提到的“伟人”更有可能是某位杰出的企业家而非纯粹的知识分子(如让- 保罗·萨特)。然而,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不同职业的人在这方面有着重大差异。
印第安纳波利斯人和纽约人重视实用型才智的原因可能与这样的一个事实有关,即他们普遍地更看重成功,而且经常将成功解释为有能力充分利用头脑的优势。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脚踏实地的房地产经纪人这样评论某些聪明人:
他们也许掌握了⼀些书本知识,可⼀旦涉及那些我认为非常简单的实际判断时,他们就会得出荒谬的结论。在商业世界,做事绝对是凭常识。它没有什么秘诀,也不深奥,不是非要有物理学家的头脑才能成为商人。
在这种情况下,才智被视为是“识别机会、抓住机会、利用机会并使之发挥作用的能力。而其他人处于同样的时间、地点和环境,却错失了一切机会”(印第安纳波利斯某房地产开发商)。
这种实用型才智观显示出美国人划定文化边界的方式与法国人的不同。法国人认为在料理日常生活方面的低能是可以接受的,如上文所述,法国男人甚至会炫耀自己在处理被认为平庸的事务时笨拙无能,而美国人对这类无能之辈更为挑剔。当然,我也确实遇到过一些欣赏知识本身的美国人,但即使是这类人,也普遍重视在日常生活中的能力和对实用知识的掌握。
法国人和美国人之才智观的主要不同,还体现在这两个群体彼此谈论对方的方式上。银行家杜托瓦和经常到美国出差的工程师路易·杜福尔概括了很多差异。在提到法国人对口才的酷爱时,杜托瓦先生解释道:
法国经理人的才智可以轻而易举地远超美国经理人⋯⋯无论是从文化、信息、教育和分析能力的层面来说,还是从他们的广博兴趣来说⋯⋯他们无疑要聪明得多。但若想成功,光是聪明、精雅和有教养是不够的。你还得务实,得知道你为什么要开会,要作出哪些决定,为什么以及如何去做。法国人不明白这⼀点。他们太爱夸夸其谈。他们对权力有⼀种渴望,并试图通过修辞来满足这种渴望。谁的谈吐最优雅,谁掌握法语最娴熟,谁说了算,谁就赢了。因而,对我们法国人来说,更聪明、更有教养是非常重要的。
杜福尔先生也认同这些观点,他觉得美国专业人士过于专业化,而且兴趣过于狭窄:
我认识的美国⼈除了工作和日常生活,对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当)他们出国时,当他们来到法国,他们最感兴趣的是刻板印象中的(法国⽣活)。(他们的兴趣)不是很多样化,而且很肤浅⋯⋯他们爱拍照,以此证明自己亲眼见过埃菲尔铁塔。他们对(社会)差异不是很好奇。(他们和我们之间)也存在⼀些积极的差异。比如,他们对工作中的人际关系(和冲突)不太在意。他们对职业生活的意义有着更严肃的理解。他们的效率要高得多。
法国职场中的那些被社会推定的才华品质,在美国职场中可能毫无用处。在法国职场中,口才、综合能力、批判意识和强大的抽象能力非常关键;在美国职场中,求实精神、注重效率、专业知识和实用主义更为重要。
自我实现
如果说法国人似乎特别强调知识分子风格,那么相比之下,美国人则更看重自我实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计算机专家鲍勃·威尔逊娶了一位音乐家,他的生活非常忙碌,在运动场和艺术圈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他在谈到成功的概念时,生动地说明了自我实现的含义:
我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种活动占满了⋯⋯所以对于那些正在实现梦想的人,我是很欣赏的。那些⽆所事事的⼈⋯⋯在我眼中没有地位。我更喜欢跟那些追求⾃我实现的人相处,我认为成功是⼀种能够找到值得解决的问题并解决它的能力。我46岁了,我想成为惠普的⾸席信息官,我有三幢房⼦,年收⼊48.7万美元,两个孩子,一条狗和一辆法拉利。这类生活,你懂的,对我来说算不上成功。⽽且,有可能在六个⽉后(我的⽣活)就会改变。我可能会发现⼀些绝对能点燃我求知欲的东⻄。我必须如饥似渴地追求,到那时再回头看我⽬前的成功,可能就不过是围绕着解决某个问题,可能是⼀件非常具体的事情,比如完成某个目标。所以我想,保持思想的活跃或许是我对成功的真正定义。
对鲍勃来说,自我实现代表着“做事”并“成功地”做事,他将这一概念与求知欲和智力活跃联系在一起。普遍而言,自我实现在这两个国家都受到重视,它被等同于才智或求知欲。正如一位信息提供者所说:
(那些不努力实现自我的人)不具备真正的求知欲。我发现他们对什么事都不投入,他们没有任何热情。我觉得这些人不太可取。我试图保留对他人的评判,直至对某⼈有所了解,你懂我的意思吗?也就是搞清楚他的才智跟我的相当还是更胜⼀筹。对于没有求知欲的人,我往往不予理睬。
不思自我实现的人被逐出圈外,因为他们沉迷于被动而平庸的休闲活动,尤其是爱看电视。确实,自我实现者中很少有人会很赞赏看电视这种消遣。印第安纳波利斯一位睿智的医学教授这样表达了他们的观点:
我觉得大多数情景喜剧都很愚蠢。有奖竞赛节目是对人智商的侮辱。我对体育运动毫⽆兴趣。我从不看体育比赛。我不觉得它有什么意义⋯⋯反正我是真没看出它有多大的价值。
一般来说,自我实现者会参与积极且有组织的活动,他们的长期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潜力:他们下棋、学乐器、锻炼、节食、去博物馆,拯救雨林,选修各种课程,等等。同样,他们也将自己的朋友描述为热爱生活的人,他们会给自己提出问题,有好奇心,还会“仅出于好玩儿而自己打造家具,买房子并翻新它,对各种各样的主题感兴趣并如饥似渴地阅读”(克莱蒙费朗某财务顾问)。正如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英俊的雅皮士单身律师所述:
那些安于平庸的人对我没有吸引⼒。真的,我对他们⼀点也不感兴趣⋯⋯你懂的,我指的就是那些不想提升自己、不想改善思维方式的⼈。出于某种原因,⽆论是社会学的、⼼理学的还是经济学的原因,他们⼀般都会陷⼊⼀种循规蹈矩的⽣活,这实在是太、太、太⽆聊了⋯⋯我不想和那些⽆所事事、坐在烟雾缭绕的酒吧里的人交往。
美国的这些中上阶层成员高度重视任何可被视作自我实现信号的活动。尤其是节食和锻炼,有些人说,他们对那些身体状况差的人会产生优越感。比如纽约的一位公务员解释道:
我喜欢在身体上和精神上都能照管好自己的⼈,那些与众不同的人。我有⼀位木匠朋友,他56 岁退休之后开始坚持跑步⋯⋯没人真愿意和那种放任自己身材走样的人做朋友。我在某种程度上倾向于同情弱者,但他也必须是个自爱的⼈。
在许多方面,这种对自我实现的关注可被视为美国中上阶层的标记:这个群体拥有参与许多文化和体育活动所需的经济资源。有关闲暇时间和育儿观的研究表明,在关注自我实现的人群中,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比例超高。一项针对不同社会职业群体的休闲活动模式研究发现,虽然专业人士和经理人大约仅占美国人口的15%,但在对“国际化”活动和自我充实(定义为提供激发才智、获得独特的和创造性成就的机会)感兴趣的人当中,38%是经理人或专业人士,而在蓝领工人、文秘和白领技术工人中所占比例分别为10%和25%,剩下的是家庭主妇和学生组的占比。同样,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看电视的时间也较少。此外,与工人阶级相比,中上阶层人士认为,将某种求知欲、探索的兴趣和自我实现的需要传递给他们的孩子是更重要的事。
当人们将自我实现作为一种高等地位信号来强调时,便可能同时划定了文化边界、道德边界和社会经济边界,将自我实现等同于展示道德品质的证明,并且是具有取得社会成功的 “正确”品格。自我实现在美国中上阶层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可以解释为:它能间接地标志一个人在道德、文化和社会经济等级制度中的高级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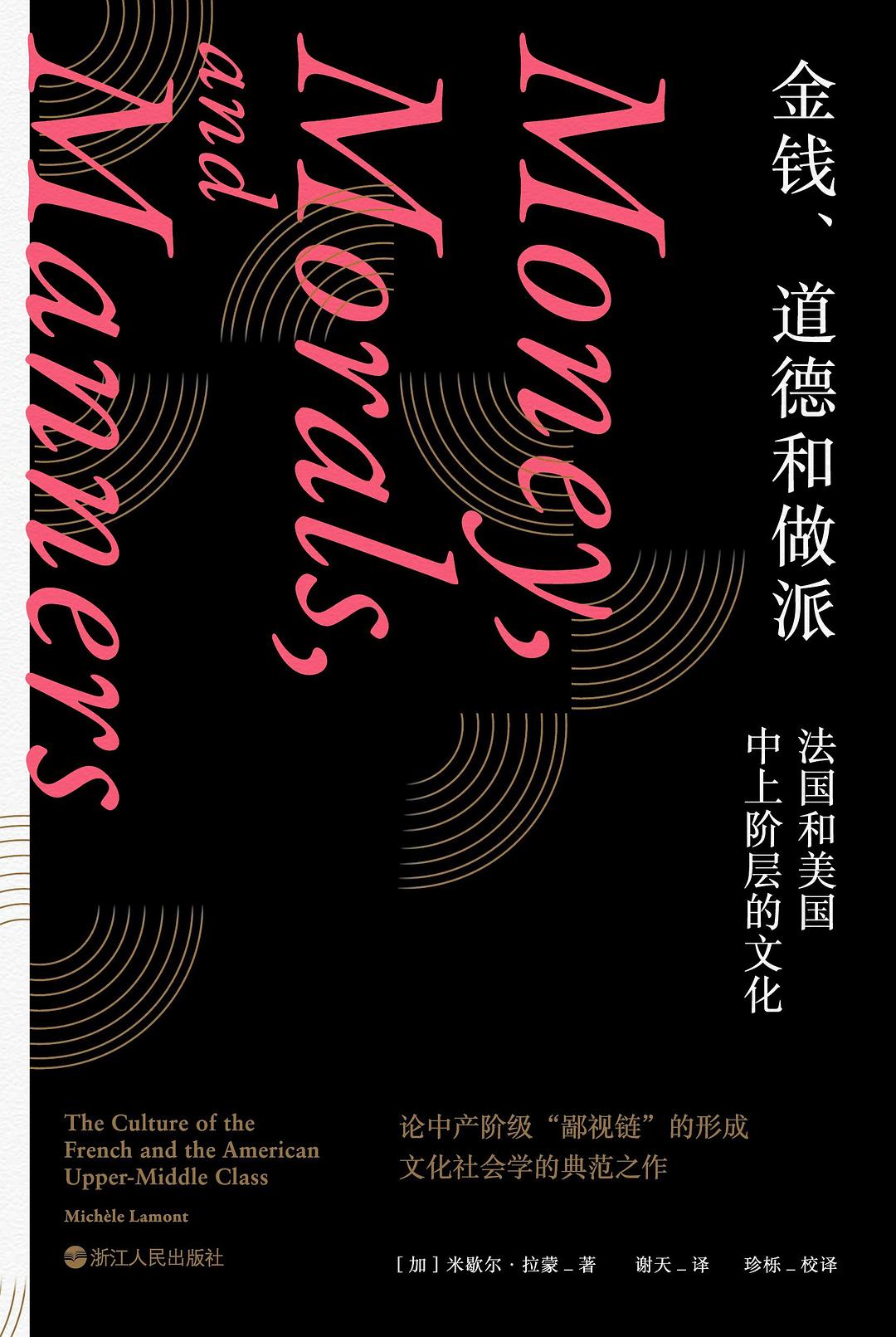
《金钱、道德和做派》;作者: [加] 米歇尔·拉蒙;出版社: 浙江人民出版社;出品方: 潮汐Tides;2024年7月版
【本文节选自《金钱、道德和做派》,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