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是家乡的魂魄,一句话就能听清一个人那深埋于地的根须。方言又是一种血脉,远走天涯,血管里汩汩流淌的还是那一腔火热。方言还是一根筋骨,连接着一方水土的气息。方言更是一丝乡愁,萦绕在心间、紧锁在眉头。
姥姥年轻的时候,她父亲带着除了她以外的弟妹们逃荒到山西。姥姥看父亲挑着担子拉着年仅十岁的妹妹越走越远,冲那背影喊:“一定要回来——”一走经年,等妹妹再回来时,已经操一口纯正的山西话了,姥姥失声痛哭:“你怎么变成‘老西儿’了啊?”姥姥认为,失了方言就真正成了外乡人。
姥姥的父亲能在山西站住脚,也得亏那一句家乡话。初到山西临汾,拖儿带女的他连落脚的地儿都没有,在火车站到处打听用人信息。走投无路时,一位说家乡话的老大哥问他是不是河北人。听见乡音,无异于看见亲人,姥姥父亲拉着老大哥的手就掉下了眼泪。在老大哥的帮助下,他被安排到了矿上工作,就此安家落户。
我也曾有过渴望他乡遇故知的悸动。年少时只身在外,实在想家了,就跑去火车站,听各地方言交织汇聚在一起,感觉并不是只有自己身在异乡。偶尔能听到几句家乡话,会兴奋地跟着人家走出很远。有一次在公交车上,几个人在交谈,听话音离我家不超过十里路,我几欲张嘴喊一声老乡,又矜持自己一个女孩子,怕被人嗤笑,最后看着他们下车远去,遗憾得只想掉泪。
我从不敢因为离开家乡便放弃方言。母亲告诉我,她有个同伴在外工作,有次回家探亲,一进门便被婶子大娘围在中间,七嘴八舌问啥时候回来的。他不动声色,等喧闹的人群安静下来,走到殷切望着他的父亲面前,清清嗓子用蹩脚的普通话说:“报告爸爸,我是昨天晚上回来的。”他眼见父亲的眼神由欣喜变成惊讶再变到愤怒,父亲抬脚脱下布鞋,照着他的屁股就是一下子,嘴里大骂:“你坐在碗上,你还坐在锅上呢!你个小兔羔子,出去两天不会说话了!”他吓得撒丫子就跑。
这个故事流传甚广,版本也大同小异。母亲用最质朴的方式在提醒我记住乡音,别忘了本分。
一次聚会,席间有朋友说起方言,他笑说他们的语言最接近普通话,而我们当地人说话一股“土腥”味道。本是玩笑话,大家一笑了之,却有一位不依不饶,非得让他说说“土腥味”是什么味儿。一顿纠缠后不欢而散,并发誓不相往来。不用怀疑故事的真实性,这个人就是我,也不用讶异我的较真,方言一直是我的骄傲,岂能容人亵渎?
其实,每一种方言里都有普通话所表达不了的东西,那种东西只有用方言说出来,才能把感情渲染到淋漓尽致。不同的平仄、不同的声调、不同的抑扬顿挫,尾音的上扬和下落,都会令人体会出不一样的心境。
有外地的姑娘嫁到我们家乡,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过去,她们早已把当地方言说得流利如常,但本地人仍能从她们的语气里听到一点点的不一样。这点不一样,来自于她们自己的根系,是她们今生舍弃不掉的烙印。
方言是刻在身体里的基因,倾此一生深扎于生命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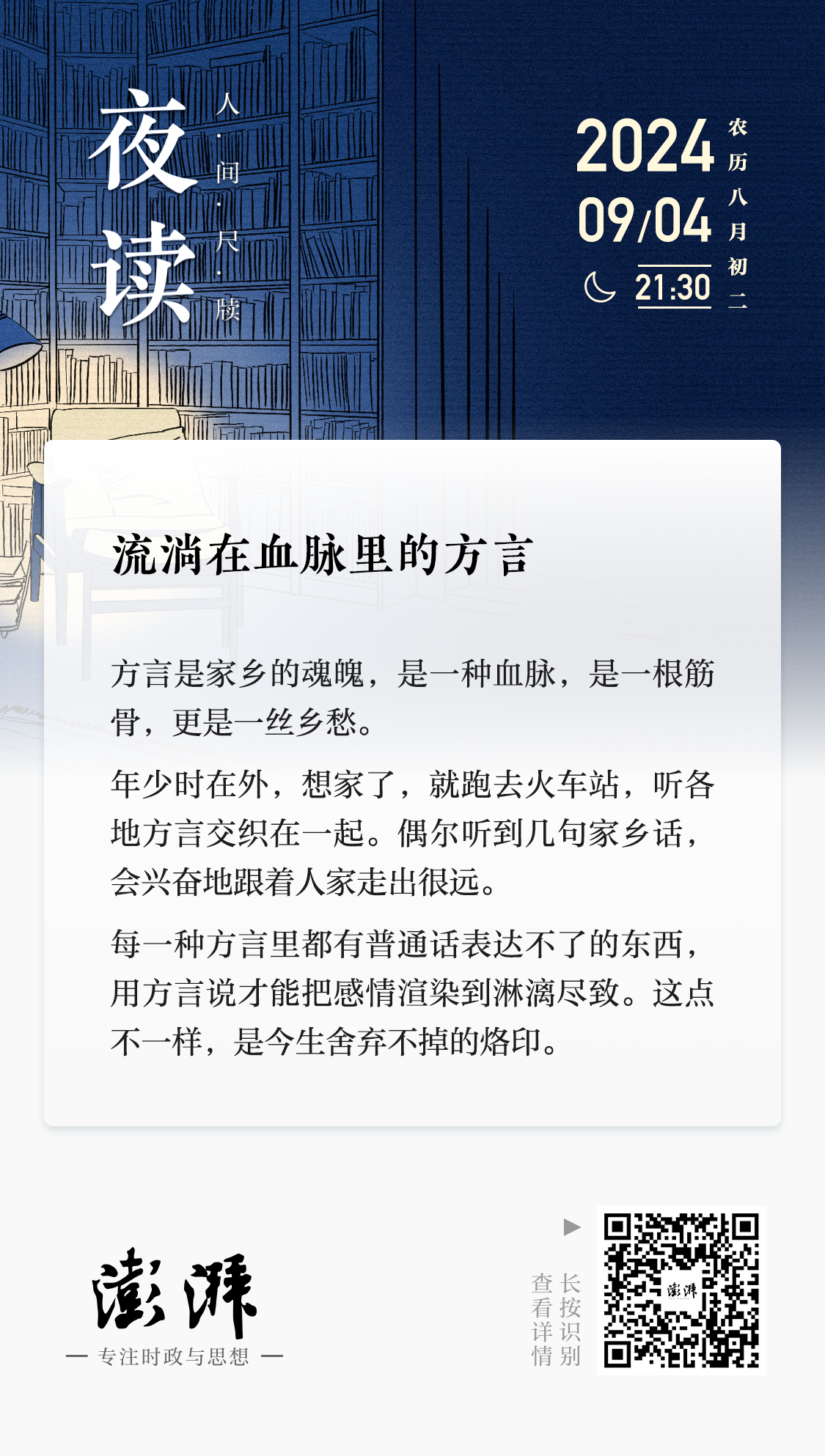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